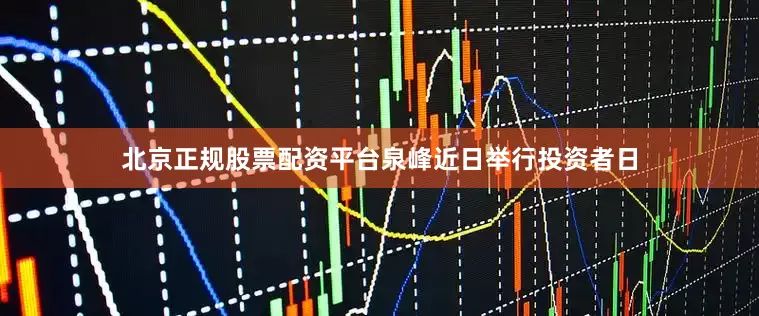“在1948年9月的某个黄昏时分,窑洞内的灯光忽明忽暗,范济生手持一个搪瓷杯,突然向主席发问:‘假如当年西安事变未曾发生,我们的事业是否就会陷入绝境?”
毛泽东将烟蒂轻轻磕入烟碟之中,沉默片刻,仅以简短的七个字回应:“现状,料想不会更糟。”这番话让在场的众人后来越发回味无穷。欲解其意,便需将时光机拨回到十二年前,回顾那场突兀间成为历史主线焦点的事件——“十二·十二”。
1935年秋季,当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,踏入甘肃南部之地时,其兵力尚不足三万。装备陈旧,弹药物资匮乏,甚至伤病治疗都需依靠山区百姓晒制的草药。长征的胜利无疑是振奋人心的,但胜利的余晖尚未散去,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便如紧缩的绳套般重新笼罩。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,形势都岌岌可危,而抗战的呼声却愈发强烈。此刻,中共中央正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:一是继续北上,深入绥远的草原地区;二是向东寻找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,寻求通路;亦或是再次踏上长征之路,翻越秦岭,进入川康地区。不论选择哪条道路,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沉重的血泪代价。

蒋介石亦感棘手。他在庐山高呼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口号,然而东三省早已落入敌手,日军铁蹄已至察哈尔边境,他却仍忙于在陕北调兵遣将。国民党内部分歧日益加剧,广东、广西、新疆等地的实力派人士纷纷抱怨南京当局只顾内战,而忽视了国难当头。张学良更是心中郁结——东北沦陷,父亲的血海深仇未得报复,自己却被迫参与围剿共产党,这其中的账目无论如何也难以清算。
1936年春初,周恩来致信张学良于瓦窑堡,援引古语:“兄弟虽有小忤,其利却在于外人。”此信辗转至张张学良之手。阅毕,张仅以“说得在理”一语回应。自此,东北军与红军在前线之冲突显著减少,暗中互通情报已成为日常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张学良并未仅限于旁观,他秘密组织骑兵训练,储备军需物资,甚至悄无声息地释放了一批被俘红军士兵。这些行为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,但苦于缺乏确凿证据,蒋介石只能将“副总司令”的头衔扣在张学良身上,试图近距离监视他。
“一条路受阻,便另寻一条。”
日军步伐加快。在东京秘密提交的报告中,关东军作战参谋指出:“若华北局势持续僵持,中国内部恐将生乱。”换言之,日本亦察觉到国内军阀与共产党间的矛盾,意图趁机扩大势力,向南进发。那一年,外患与内忧犹如两把紧握的剪刀,不断地张合,压迫得人人喘不过气来。

在当时的形势之下,张学良与杨虎城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策略。在十二月的那个黎明,张学良的卫队将临潼华清池团团围住,蒋介石匆忙逃往山上,在被强制带回时,脚下仍留有枯草的痕迹。蒋介石愤怒地拍案怒斥:“你们究竟意欲何为?”张学良平静地回应,“请委员长将枪口转向敌人。”这句坦率之言不仅改写了历史进程,也将所有涉事者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必须携带王稼祥和林伯渠同行,“此次谈判非同寻常,需有备选方案以备不时之需。”有趣的是,斯大林方面也发送了电报,含糊地建议中共不要杀害蒋介石,以免激起日本全面南下的冲动。这一事实充分说明,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的关注程度远超以往对中国内政的预估。
保留蒋介石的生命,共同抗日。
若非这次拘押,红军是否会被蒋介石的围剿所击溃?

审视兵力对比,1936年年底,胡宗南与薛岳两部共计约三十万之众,加之空军与炮兵的支持,相较之下,陕北红军仅有不足四万,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。然而,红军已在黄土高原建立了广阔的游击区,群众基础稳固,交通线既短又隐蔽。更为关键的是,国民党各部队将领间相互制约,真正能够对陕北构成合力者寥寥无几。一旦战线过长,补给问题将反噬蒋军。此时,毛泽东已部署“化整为零、灵活机动”的战术,旨在将敌人拖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
审视政治局势,广东与广西的新军与南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。李宗仁在私下里向中共表达了他的立场,即“不反对抗日”。在新疆,盛世才已经与苏联建立了联系,而四川的刘湘则明确表态“抗日当先”。蒋介石试图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在陕北,然而这一目标几乎难以实现。换言之,即便中共被迫进行第二次转移,他们仍有可能在西北和川北地区稳固脚跟。随后,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爆发,中共有可能将斗争的重点从内部转向外部。
不容忽视的是经济与舆论形势。1936年,《大公报》与《申报》每日以大量篇幅热议“外患迫在眉睫,内战亟需停止”。知识阶层与学生群体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冲突的容忍度已降至临界点。若蒋介石再度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,必将遭遇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,财政亦将因军费开支而陷入困境。权衡这些因素,毛泽东才敢于断言“形势不会比目前更糟”。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极高的历史必然性,只是其形成的方式与时间点或许会有所不同。

即便从红军的立场出发,设想最不利的情况。即便陕北的根据地遭受摧毁,主力部队南撤至川康地区,凭借山地的天然屏障和群众的游击战术,日军难以深入山区,而国民党军队也鞭长莫及。美国军事顾问史迪威在其后来的报告中指出,“山地游击战是任何现代化军队的噩梦”。这一论断恰好验证了毛泽东对持久战的预测:敌人进攻时我们撤退,敌人疲惫时我们反击——时间永远站在那些善于移动的一方。
重返窑洞中那盏时明时暗的煤油灯下,毛泽东对范济生的简短七字回应,透露的并非仅仅是自信,更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力量对比的深刻冷静分析之上。西安事变无疑缩短了时间,促使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前,但它并非是唯一的契机。换言之,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、全国范围内抗战情绪的日益高涨,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失衡,这三股力量终将迫使蒋介石走向合作的道路。即便没有西安事变,也会有其他“事变”发生。
结局,我们皆有所耳闻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,抗日战争的爆发,历经八年的磨砺,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历史上每一个关键节点的走向,往往并非由单一事件所决定,而是无数力量汇聚叠加后的“临界点效应”所使然。毛泽东那句“情况不会比现在差”,正是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格局的精辟概括,亦是对自身战略储备的坚定信心。如今重读,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坚定与冷静。
配资手机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相关网址4. 原有品类的差异化迭代
- 下一篇:没有了